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出发,分析了娥苏拉勒瑰恩的《道德经》英译本,文章认为娥苏拉勒瑰恩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对原文的阐释和重写和译者身份重塑两个方面对《道德经》进行了翻译,译作的实际呈现与原作相比有不忠的部分,也因此使译作焕发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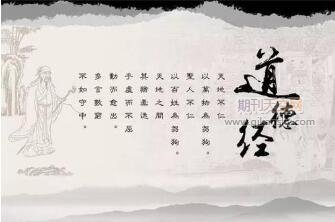
关键词娥苏拉,《道德经》,女性主义
1.引言
道德经是我国古代伟大哲学家、思想家老子的传世著作,承载着中国深厚的传统哲学文化。同时道德经也是中国译介到国外出版版次最多的一本名著。国内研究道德经英译本的角度不断推陈出新,涉及语言、哲学、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道德经共81章,分《道经》和《德经》,主要从论道、治国、修身三个方面来阐述老子的思想体系。
道德经所用的词句简练却所含万象,语义含糊使得每一个版本的翻译都有自己的阐释空间。老子用诗韵的语言,睿智的哲学探讨了宇宙的形成,君子的品德和治国齐家修身的策略。《道德经》中使用了丰富的女性主义意象,如“玄牝”“谷神”等,提出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重要哲学观点。刘静(2009)[1]指出《道德经》的英译经历了三个高峰:16世纪理雅各以归化为主,旨在将《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相融合,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道路;后期亚瑟·韦利传播中国文化以攻克西方宗教中的漏洞与弊端,极大程度地保留《道德经》原文的意思,不惜牺牲其本来的诗;第三次翻译高峰中以林语堂为代表,兼顾诗学和内容。而在第三次翻译高峰中,冯家富与其妻简·英格里希翻译的《道德经》首次有女性译者参与。随后开始有女性译者独立翻译《道德经》,如陈张婉辛(EllenMarieChen)、娥苏拉·勒瑰恩(UrsulaLeGuin)等[2]。本文旨在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的角度,从对原文的阐释和重写以及译者身份重塑两个方面分析勒瑰恩《道德经》英译本,进而探寻《道德经》英译本在误读和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前提下的重生之路。
2.译者简介
娥苏拉·勒瑰恩(UrsulaKLeGuin)是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其作品《黑暗的左手》(TheLeftHandofDarkness)与《一无所有》(TheDispossessed:AnAmbiguousUtopia)均获得了雨果奖与星云奖。《黑暗的左手》中娥苏拉描述了一个没有性别之分的星球,人人皆可受孕,也就没有了男权主义和俄狄浦斯神话。强/弱、支配/服从,主宰/奴役等等西方的二元对立现象,都通过娥苏拉巧妙的性别解构而弱化甚至改变[3]。
娥苏拉在其英译《道德经》的序言里写道她的父亲,美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勃(AlfredKroeber)经常阅读保罗·卡鲁斯(PaulCarus)的《道德经》译本,并常常为自己喜欢的章节备注,希望在自己的葬礼上纪念诵读。《道德经》对娥苏拉的影响在其作品中有非常明确的体现,比如在《黑暗的左手》中艾斯文(Estraven)直接使用了“阴”和“阳”的概念做了一首诗,里面写到“光明与黑暗,互为左右手,生存与死亡,本来就同源”;《地海传奇》系列中“无为而治”的大魔法师;科幻小说《倾诉》中的女主人公通过道家的“对话性思想”,与警官这一“他者”的形象进行沟通,才克服偏见,走向成熟[4]。其他的作品中都多次使用道家思想。
《道德经》中虽然有较大篇幅的对女性和生殖崇拜的描写,老子有意使用“雌性”隐喻解释宇宙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运行,表明这些隐喻不仅具有描述性意义,也有规范性意义[5]。因此《道德经》中的“雌性”隐喻与性别的二元对立无关,只是为了使老子的哲学更加形象和圆润。然而归根结底,《道德经》的写作对象始终是针对掌权者,也就是男人,只是老子使用“雌性”的隐喻使自己的哲学更容易被接受[6]。
《道德经》并不是一个女性文本,却因为娥苏拉积极主动的阐释而有了新生。这也是娥苏拉对“道”的追求,而她对“道”的追求与她的女性主义理念息息相关。娥苏拉的《道德经》英译本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反响,笔者认为用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其《道德经》的英译本可以更深刻理解其翻译思想和创作理念,同时勒瑰恩的误读与创造也为“道”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得其在西方以及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中心论和二元论,因此一直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都认为译者应该是中立隐身的。译本是原作的附属物,同女性一样被推到低等、贬斥的边缘地位。女权主义本身是政治行为,是女性为争取政治、社会、文化上的平等而发起的连续的历史活动。它激烈地批评已存的写作方式和使用语言,使用新词,新隐喻和新排版、注解等远离原本的男性主义文本。
女性主义对翻译也持同样的立场,认为如果重复讲男人故事,使用男权中心的语言,那么女性依旧是他者,女性的语言依旧是边缘化的。传统译论中,译者由原作之“源”所决定,所以译者是依附性而非创造性的。译者在传统女性角色中获得了自己的反照,同时女性也在译者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对应。[7]相对的概念因此产生,并且造成了固话的意象。
现代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更大程度的强调差异性,以及彰显女性作为译者的主体性。解构大师德里达曾经创造一个词“延异”(differance),包含“相异”与“延迟”两个意思。“相异”是空间概念,表示符号的差别和分裂;“延迟”是时间概念,表示符号的替代被无限制的推后。语言是符号,而符号的不断变化运动导致中心论的稳定性遭到质疑,不同的中心持续替换取代,延异则是一种阐释替代另一种阐释的动态过程。该词对原本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的解构,深刻动摇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确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此为基础,倡导差异哲学,通过强调差异,否定单一权威和权力中心,重新构建性别[8]。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目的在于(1)消除原文乃至译文中对女性和女性译者的贬低。(2)重新定义译作和原作的关系。根据互文理论,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本,译文和原文相辅相成,包括原文都不是绝对的原创[9]。译文和原文地位平等,译文绝非附属,而是原文生命的跨时空延续[10]。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通过翻译重塑女性形象,对传统的“忠实”定义进行解构,以积极姿态对文本进行干预,挪用、操纵甚至重写。译者凌驾于原文之上,对原文使用篡改手段。旨在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和女性意识。“重写”或“劫持”(hijacking)虽然是最富争议的翻译手法,也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极力倡导的翻译策略,因为其对“忠实”的理解与结构主义不同,它解构了意义,认为意义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考虑到译者的主观意识,可以进行再创造。
4.娥苏拉勒瑰恩女性主义在道德经中的彰显
作为女性作家且深受《道德经》哲学思想的影响,娥苏拉在其作品中总是融入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和道家思想。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DMurphy)在其开启了生态女性批评与实践的集大成之作《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与批评》中极力赞扬了娥苏拉的女性主义作品。并在其访谈中指出娥苏拉的《一无所有》中所倡导的“对话”的方法也是他所强调的。因为在对话之中,“支点”在不断的变化,和以往的二元对立完全相反。在《道德经》的翻译中,娥苏拉增添了大量的副文本,凸显了其女性译员的主体性,并对译本进行有意识的删减添加,创造性地使用诗的语言形式,并巧妙地变换主观意义,使得其《道德经》的译本成为具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新生文本。娥苏拉女性主义理念指导下的《道德经》译本解构了传统译论中对“忠实”的定义,也是对现代翻译标准的革新,这种革新在其译本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4.1.打破翻译的从属地位——对原文进行重塑
香港教授刘笑敢曾经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道德经》是一部用男性语言写给男人看的书。然而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娥苏拉等女性译者包括部分男性译者如史蒂芬·米歇尔(StephenMitchel)开始使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这一新的视角来阐释《道德经》。现代阐释学认为人文科学必然具有历史局限性和差异性,不同的作者或者译者由于历史时代不同和角度不同,所理解的文本意义也不尽相同。娥苏拉在《道德经》译本中以其父钟爱的保罗·卡鲁斯(PaulCarus)的译本为底本,并参考了数十种英译本[11]。娥苏拉本人并不通中文,也在开篇说自己的这一译本其实并不是翻译,而是摹写(rendition)。受个人女性主义思想的以及多种译本的影响,娥苏拉在摹写的过程中,大胆的对原文进行了阐释、重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句法、语义和文本中均有体现,可归纳如下:
4.1.1.译本内容的阐释和重写——消除二元对立
不同于其他译者,娥苏拉在每一章《道德经》的译文中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命名,有些章节的命名是对译文的概括总结,比如第三章为“安静(hushing)”;而有些章节的命名给出了作者的解释,比如第十九章“素绸与朴木(RawSilkandUncutWood)”,娥苏拉在脚注中说“素与朴通常指的是简单与自然。”除了对章节进行创作型的命名之外,娥苏拉在部分章节中也进行了阐释和重写,如第61章,原文意思是:大国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以女性的雌柔对小国包容,因为雌柔就是因为其安定且柔弱,屈于雄强之下,才能胜过雄强。大国对小国怀柔,则能控制小国;而小国对大国附耳顺从,则能为大国所容。大国不要过分想统治,小国也不要过分顺从,两国各取所需,最好还是大国对小国包容。
从《道德经》原文可以看出,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和平反战的,因此老子对掌权者的规劝都是希望他们能有女性的温柔。然而在娥苏拉的译本中,她明确在引言中说明尽管大部分学术性译者的译本都强调“圣人”的权威和男性力量,将道德经作为统治者的行为准则,自己却希望自己的译本更适用于现代,适用于并不聪明,并没有掌权也不是男性的读者,她不追求内行的秘密,只寻找灵魂的声音。娥苏拉认为《道德经》可爱迷人,热诚且让人感觉新鲜,所以在第61章具有明显治国理念的章节中,娥苏拉选择了删减和增补,除了第一节用了政体(polity),第三节使用了两次“country”,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国家的明确字眼。而最后一节老子对于执政的总结,认为两种类型的国家各取所长,而大国应该包容小国为佳,被娥苏拉直接删除,直接阐释为“居下流者为高位,处高位者居下流(lielowtobeontop,beontopbylyinglow)”。娥苏拉对原作的阐释和重写使得这一章节不像是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劝谏方,而是适用于每个人的处事原则。
推荐阅读:降水论文发表在什么期刊上?
娥苏拉在其《道德经》的译本中打破了原有的翻译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两性关系的二元论是女性主义的重要议题之一,娥苏拉曾在其小说《倾诉》中打破性别登记,勾画了一个没有特别性别要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阿卡星。可以看出娥苏拉认为万物平等,传统的二元对立价值观会导致冲突和不平等。因此在《道德经》的译文中,娥苏拉通过阐释和重写,巧妙的转移了原文固定的“男性”或主导意象,展现了其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即承认差异并在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和谐与平等。
4.1.2.译本语言形式的模仿和突破——娥苏拉的整体论思想
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的哲学就是“知雄守雌”的整体观,而西方的女性生态主义与老子的哲学的最高追求是一致的。女性主义在批判二元对立之外,强调从整体出发,认为世界是“宇宙之链”,一个平等多元且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需要每一个环节的和谐统一,因此在这个“宇宙之链”中每一环节都直接或间接地紧密联系[12]。
娥苏拉在自己所参考的十多种《道德经》译本中发现,《道德经》部分是散文,部分是诗节。大部分她所阅读的译本都只有《道德经》的内容和意义,却流失了诗的美。英语译者由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或宗教目的,将《道德经》的意义截取并按自身需求塑造西方的《道德经》思想,以求通过老子的精神来解释或解决西方文化或宗教中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译本往往不会注意到中文本身的语言美,从而也就丢失了《道德经》中重要的诗学。然而对于诗来说,美不是装饰,而是核心,也是《道德经》思想的重要一部分。同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的史蒂芬·米歇尔(StephanMitchell)评论《道德经》言辞优美,是世界一大奇迹。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来说,传播其哲学思想的最好方式就是以诗一般的语言。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上指出,中国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诗化哲学。在此的诗化哲学并不只是孔孟老庄的哲学中的诗意,更是诗文中的哲学思考,哲学应该和诗一样,赐予有限生命中最重要的特征。
娥苏拉也认为诗学并不只是韵律、音步或者语言的特定紧密组成形式,而是综合统一在一起的所有即是诗学。因此她在《道德经》的译本中,充分发挥女性译者的主体性,重新定义忠实。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译者的理解是原文的延伸,因此解构了对原文忠诚的一元论。然而娥苏拉参照的底本—保罗·卡鲁斯的译本却极度忠实,完全直译,甚至不考虑英语写作的习惯,并且在汉字旁注明英语对应词与注音和解释。卡鲁斯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因此译本及注解也充满了浓重的宗教情怀。娥苏拉的译本模仿与突破交织,形成了自己译本风格的统一,以第62章为例,娥苏拉命名为“道的礼物(Thegiftoftheway)”,在其中娥苏拉采用诗的形式进行分节,并且用了“对话”的方法解构了原文中“二元对立”的男权语言。原文本意为“天子加冕,设置三公的时候,有拱璧在前驷马在后的献礼仪式,还不如把‘道’献给他们”,而娥苏拉巧妙地使用了第二人称,并将焦点集中在第二人称,坐进此道的男性形象,被解构成了不如献道给天子的,不分雌雄的形象。且在最后“有罪以免”中没有使用男性语言,如“罪”或“逃”,而是以另一个视角,选择使用“庇护(shelter)”。
原章节42个字,英译版43个词,紧密贴合原文的同时也做了自己的调整和修改,对仗工整,有咏叹一般的诗感。娥苏拉通过紧密贴合原文的诗学并巧妙创造自己的诗韵,展现了其女性主义的整体观。
4.1.3.意义可变——使用中性语言解构男性形象
女性主义认为“原文和译文都是不同的能指符号”,原文是译文的延伸,因此也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阐释方法,老子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时期,当时战乱频频,老子看着生灵涂炭,悲天悯人,于是塑造出一种理想化的完美人格——“圣人”《道德经》总共81章,共出现过32次圣人,大部分情况代指统治者,也是老子实施教化的对象,只不过老子使用大量的雌性隐喻以期统治者能够怀柔,减少战乱。娥苏拉所参照的保罗的译本以及亚瑟·韦利的译本都认为《道德经》是西方世界基督教的填补,因此在他们的译文中多次将“圣人”译为sage、theholyman、thesaint等等具有明确基督教意象的词。对此在开篇娥苏拉即指出sage不是她所理解的圣人,她也不想强调圣人的男性化以及统治权力。因此在娥苏拉的译本中,主要使用了中性的语言,将sage翻译成thewisesoul,或者thewise,部分章节还翻译成复数,从而解构了圣人独一无二的形象,变得亲切而大众。在第七十二章中尤为明显: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译文:“Whenwedon’tfearwhatweshouldfear,weareinfearfuldanger.Weoughtnottoliveinnarrowhouses,weoughtnottodostupidwork.Ifwedon’tacceptstupidity,wewon’tactstupidly.So,wisesoulsknowbutdon’tshowthemselves,lookafterbutdon’tprizethemselves,lettingtheonego,keepingtheother.”
老子撰写《道德经》其实是给掌权者阐述自己的理念,这里在描述“民”和“圣人”的时候明显用了区别化的处理,所指的圣人也是男性,体现了当权者无可置疑的地位。娥苏拉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译者,将“民”译为we,圣人则用了复数“wisesouls”,不带任何性别和权力中心论的意味。除此之外,娥苏拉还使用了劫持(Hijacking)的手法,原文指的是如果逼迫人民不得安居乐业,压迫人民,会导致他们反抗统治者,而在此处娥苏拉使用第一人称,以人民自己的口吻表达需要安居乐业的愿望。“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更是翻译成如果不接受愚蠢行为,那我们也不会做蠢事。娥苏拉操控语言,将原本劝诫掌权者怀仁的男性语句翻译为强势的女性语句,圣人不再是独一无二且具有唯一权力的形象,而是具有自知之明,毫不自夸的评价对象,这样强烈的女性主义用语在娥苏拉的《道德经》中比比皆是。



